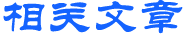两次进京上访的经历和认识的升华
1999年国庆节放假期间,我听说有的大法弟子进京护法了,法不正,不回家。我当时认为进京护法的行为是符合大法的,但是在法理上又说不出来为什么进京护法是符合大法的,也就是在法上还没有理性认识。怎么办呢?我决定自己先在行为上符合法──进京护法,至于在法上还没有认识到,那么就在护法的过程中去理解、去认识。
1999年10月17日我来到了北京,很顺利地就和先来的学员联系上了,大家住在一起,经过十几天的集体学法,我对于进京护法,在法上有了真正的理性认识,这也为后来坚定闯关打下了基础。10月28日我决定去国务院信访办护法、讲清真象。在路上被单位的人截住并强行带回他们居住的某单位招待所二楼,在招待所出现了几次去厕所时跳窗脱身的机会,但都在“要稳当点”、“在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”,等等后天观念的影响下没有走脱。因为我在常人中属于“不打无把握之仗”的那种人,很少做无把握的事;无论什么事,只要做就要做成,否则不做。由于在以前的修炼中没有修掉这一后天观念,从而致使这一观念阻挡我丧失了几次脱身的机会。
到了晚间,他们有两人带我出去办事,在下车时,我拔腿就跑。我在日常生活中属于跑得比较快的人,但是跑出去最多100多米,两条腿就变得像木头一样不听指挥,一步也动不了,结果被单位一位50多岁的老警察追上,并和另一人共同把我带回。他们怕我走脱,当晚带我坐上了返回的火车。在车上,我心里充满了悔恨,恨自己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错过了几次非常好的脱身机会。我在心里喊着自己的名字说:你修得太差了,可是差不要紧,自己得抓紧提高,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绝不向邪恶低头。
回到家庭所在地后,由于我不按单位的要求做,不写保证书、悔过书,被单位送进了公安局看守所。在被拘留的当天,我就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:1.无论任何时间、无论任何地点、无论任何场合、无论任何条件,绝不写保证书、悔过书和其它任何材料(其中包括修炼体会和弘法、讲清真相的材料,以防止邪恶断章取义。)。2.无论任何时间、无论任何地点、无论任何场合、无论任何条件,绝不从我的嘴里说出不符合大法的话。我同时在心里告诫自己:以上两条是绝对符合大法要求的,对于这两条以后不要再悟、再考虑了,因为再悟、再考虑,很可能就会被邪魔钻空子。
被拘留后的几天里,我脑子整天都在翻“没有脱身”这件事,思想充满了悔恨、懊丧,甚至背法时都不由自主地“走神”去想,这种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,连续持续3~4天,干扰得我几乎都不能背法了。后来在学《论语》时是师父点醒了我,师父说:“有些人甚至不敢正视,不敢触及,不敢承认客观存在现象的事实,是因为这些人太保守,不愿改变传统的观念去思维。”我发自内心地对自己说:“你现在在哪呢?在监狱呢,那么能不能因为你后悔、懊丧,而让你出去或长功呀?肯定不能,那么此时懊丧、悔恨的这种状态,除了干扰修炼而没有任何其它的作用。”此时我悟到了,没有把握住机会脱身和没有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,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,此时要敢于在法上正视、触及、承认这个事实,这才是提高的关键。我还悟到了大脑中不断地反映出懊丧、悔恨的思想念头是强烈的思想业在干扰,在北京的这个环节没做好,要承认它并引以为戒,现在在看守所里要扎扎实实地修好每一个环境、过好每一关。此后我的思想中无论再出现后悔的状态,还是翻一些应该脱身却没有脱身的“镜头”,我都坚定地抑制它、排斥它,结果只用了一天,这种强烈的思想业的干扰就消失了。
看守所里先后被关进了近20名大法弟子,我所在的监号共30多人,其中有4名杀人犯,而大法弟子只有我1人。开始时环境很恶劣,但是由于我用大法弟子的善来对待他们,并不断地向他们讲清大法的真象、揭露邪恶的新闻媒体的恶毒造谣,所以他们逐渐改变了对我的迫害和对大法的排斥、误解,甚至有几个人表示释放后要修炼法轮大法。元旦每个监号选1名文明个人,他们一致推选我,但是看守所规定法轮大法学员不准当选,所以只好作罢。狱中的生活条件是恶劣的,每天只允许去四次厕所;由于每人睡觉只有半尺宽的地方,所以被压的胸疼;除了睡觉和每次不足半分钟的去厕所时间之外,其余时间全是坐在冰冷的地上;一个半月没有洗手、洗脸、刷牙;浑身散发着臭味,手离鼻子一尺远就可以闻到强烈的怪臭味;虱子泛滥成灾,白天夜里在身上乱爬,搞得整夜睡不着觉。
由于长期坐在地上,我屁股着地的地方溃烂了,裤衩粘在肉上,每天去四次厕所就要扒四次皮,疼痛钻心啊。于是我默默地对自己说:密勒日巴当年修炼时,后背烂了几个洞,他是他那一门的弟子,而我是大法修炼的弟子,我要比密勒日巴做的还要好。正念一出,疼痛也不那么厉害了。因为没有书,所以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外,其余时间我几乎都在背师父的法,浪费一分钟都觉得非常可惜,由于我时刻用法来占据自己的大脑,不给任何邪恶钻空子的机会,所以任何邪念、邪悟,在我的大脑中都没有市场,我每天都能感觉到在法上的升华。我经常告诫自己:这次得法修炼圆满的机会一旦错过,生命的永远将不会再有了。每天除了背法外,我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把生命献给师父”,这句话一直伴随我到今天。
一个多月后,很多学员(包括一些辅导员、负责人)由于吃不了苦,顶不住压力或由于邪悟或由于大法弟子内部败类的邪恶误导,相继写了保证书、悔过书,出去了。而我无论面对邪恶的迫害、名利的引诱、恐吓和亲情的干扰(年近八旬的老父下跪大哭)始终不低头。此时,邪恶的公安决定劳教我,并且故意把消息传到我的监号里,企盼我低头、妥协,可是他们最后的邪恶伎俩仍然没有得逞,我仍坚修大法不动摇。
两个多月后,由于劳教未获批准,我被无条件释放了,我凭着对师父、对大法坚定的心,堂堂正正地走了过来。
针对此次过关,上升到法上的认识如下:
1. 在邪恶的考验面前,要牢牢把握自己的主意识
我们在炼五套功法的动作时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修炼,而在面对邪恶的考验时更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修炼。我被单位的人带到招待所后,有几次脱身的机会没有走成,不但是受后天观念的干扰,而且也是主意识不够强的一种表现;虽然当时认识到了应该抓紧时间脱身,但就是犹犹豫豫,始终没能用强有力的主意识支配自己迅速脱身。师父给安排的脱身机会一旦错过,那么就等于打乱了师父的安排,但作为弟子还要继续修炼提高,那么师父还要再从新安排以后的环境。所以在修炼中每时每刻都要高度的清醒,时刻都要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,时刻用自己清醒的、强有力的主意识支配自己,在法上认识到后就要立刻去做,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。
2.要突破修炼中的依赖性
7.20以前,修炼中有什么问题,大家可以在学法组共同切磋、探讨,但由于相生相克的理的存在,有的学员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了修炼中的依赖性。每当遇到问题、矛盾或由于一个新的环境的出现,而不知道自己应怎么做时,总是热衷于和别人切磋,并把切磋后的认识作为自己的真正认识,还有的学员甚至跟着辅导员、负责人“走”,看到辅导员、负责人怎么做,自己就稀里糊涂地跟着怎么做,做的是否符合法,自己也不知道,完全不是凭着自己明明白白在法上的体悟去做。其实,真正起指导作用的只有师父的法,同门弟子的各种体悟、认识,只能起借鉴、引导作用,自己的提高应该由自己牢牢地把握,不要把自己的提高、过关寄托于和别人的交流或寄托于别人的体悟,而应寄托在自己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上。
3.修心断欲难、明慧不惑更难
师父在《坚定》中说:“修心断欲、明慧不惑乃自负”。在修炼中面对个人利益的损失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,以及名、利、情的各种干扰,要想达到不动心,已经很难。但是在严厉的考验面前,能及时的悟到自己该怎么做,就更难;在那些表面用师父的法做依据,而实质上却是破坏法、背离法的所谓“更高层次的认识”面前,要能真正识正邪、真正地做到明慧不惑,也是更难。
有时当你悟在法上、做在法上时,方方面面的表现很可能给你造成一种错觉,使你感到好像没做在法上;甚至有时再加上有的辅导员、负责人走向邪悟,没做在法上,这就更给你弄得真不真、假不假的了,这时就看大法弟子能不能明慧不惑,坚定自己的体悟不动摇。大法弟子在邪恶的考验中做在法上时,有时不但要承受来自邪魔的压力和迫害,甚至还要承受来自走向邪悟的那些人的压力。
2001年春节前的一天,我决定再次去北京护法、证实法,因为我觉得我做为一名大法弟子在世间修炼过程中,如果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上为师父、为大法喊出自己的心里话是一个遗憾。
临行前,我对功友和家里亲人说:我证实完法后决不让邪恶之徒把我控制住,我要抓住一切机会脱身,决不会像前一次那样丧失脱身的机会。
2001年1月19日,我顺利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,在广场中心,正对着天安门大门洞的旗杆下,我双手高举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横幅,以我最大的声音喊到:“法轮大法好,还我师父清白。”紧接着我就大踏步地高举着横幅,边走边喊向纪念碑走去,走了大约十米才被扑上来的恶警、便衣和被恶警收买的、在旗杆下照像的个体营业者,夺下横幅,强行推进警车。大约二十分钟后,警车载着我离开广场。我被带到了广场东侧的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,此前我一直寻找机会脱身,可是没有找到。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是大陆最邪恶的黑窝,去天安门证实法的学员被抓后,都要被带到这里,说家庭地址的学员,交当地驻京办;酷刑折磨仍不说的学员被转到各个看守所。
下车被带进分局大楼后,我特别注意走过的线路,以便防止脱身后走错路。我被带到走廊最尽头的一个房间,屋里包括我共有3个大法弟子,对门是厕所。由于我早就听说他们对不报姓名、家庭住址的学员,根据口音分组,然后照像、录像,让各个地区来认人。所以来到这里我没有说家乡话,而是把广东、北京、山东等口音和在一起,混合着说,搞的警察也弄不清我是哪里口音。在警察交接工作时,我们三人进行了简短的交流,并共同决定不说姓名和家庭地址。我对他们说:不说姓名地址,从表面的人这看,虽然迫害可能严重一些,但至多押一周也就被释放了;而如果说了姓名地址,就要被送回家庭所在地被拘留或劳教,家庭、单位等等都要受到影响。如果这样认识是不符合大法的,我们应针对这两种表现,从法上去认识法,那就是:我们不说姓名地址,只能被压在北京,那么由于公安的条件有限,而大法弟子却很多,他们关押我们就没有条件关押别的学员,打我们、迫害我们,就闲不出手来迫害别的学员。但如果说了姓名地址,不但我们要被送回家庭所在地被继续拘留、劳教,家庭、单位还会受影响,同时他们也会闲出监号关押别的学员、闲出手来迫害别的学员。也就是说:说了姓名地址,就等于给邪恶提供了一个迫害自己和其他学员的条件。
此时从其它房间传来了毒打大法弟子的声音和学员的惨叫声,有的弟子被打得满脸是血,被强行带到对门的厕所去洗。有一个学员说:如果不说姓名地址会被打得很重的。我又对他俩说:修炼不就是个苦吗?横下一条心顶过去,就没有过不去的关;师父在《道法》中说:“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”。而觉悟了的本性(也就是已经修成的神的一面)在起作用时,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,那就是:我们人的一面,要符合自己所在境界的法的要求。所以,被打时不要一味地忍受,要不停地向他们弘法、证实法、揭露邪恶,实际上也就是在给他们说法,如果他们还有善念,这个说法的过程就是在挽救他们,如果他们已无善念、不可救药了,那么在说法过程中,我们觉悟了的本性(也就是已经修成的神的一面)自然就会去铲除他们。相反,如果我们在被打时一味地被动忍受,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人的一面在抑制我们神的一面了,在这种情况下,神的一面是不起作用的。
这时警察交接完了任务,开始对我们三人进行问话,我们三人在不说姓名地址的前提下,共同向他们弘法、讲清真象。大约二十分钟以后,出现了脱身的机会,我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,堂堂正正地从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大门走了出来。从在天安门广场打开横幅开始,到从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走出来为止,大约只用了四十分钟,时间虽然短暂,但是却惊心动魄。由于是春节前夕,因此我应该乘坐的返程列车都爆满,连站票都没有,但是我还是顺利的上了车、到了家。
值得一提的是,在我认识的大法弟子中,有四人比我早几天进京护法,先去的两个人走前说:“我俩半个月就回来”,果然半个月后他俩回来了。第二个去的学员走前说:“我一个星期就回来”,一个星期后他真的回来了。另一个学员走前说:“我四、五天就回来”,四天后他也回来了。我临走前说:“我证实完法后决不让邪恶之徒把我控制住,我要抓住一切机会脱身,决不会像前一次那样丧失脱身的机会”,结果我真的把握住机会脱身回来了。
针对此次过关,上升到法上的认识如下:
师父在《理性》中说:“用理智去证实法、用智慧去讲清真相、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”。我此次的表现是在当时所在的境界中,充分运用了一个大法弟子的理智与智慧的体现。但是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表现,如果在更高境界中看我当时对法的认识和表现,仍有很大的不足,那就是:宇宙中旧的势力针对大法弟子的一切安排,师父都是不承认的,我做为一个大法粒子在修炼中,无论是在对法的认识上,还是在证实法、讲清真象的行为上,都应坚决的抵制、排斥旧势力的一切安排;而我当时进京前在法上的认识是:“决不被邪恶控制住,要把握住机会脱身”,而要想“脱身”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,那就是“被抓”,所以,这种“把握机会脱身”的思想认识,在无形当中给自己设计了一个“被抓”的结果。尽管当时在行为上我完全按照自己的认识去做了、并且坚定地做到了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,如果我当时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认识法,认识到我是大法弟子,在天安门广场证实法、讲清真象、铲除邪恶,是当前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,邪恶不但是最害怕的,而且也是动不了我的,我决不会被抓、被带走,邪恶之徒在我无坚不摧的正念面前只有退缩和害怕;证实完法后,我一定会顺利、安全地离开广场”。如果当时我在这个境界中去认识法、并且按照这种体悟、认识,坚定地去做,那么就很可能会有另一个更加动人的故事产生。